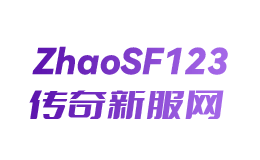
达妮出嫁
那是一个远房表亲的女儿(达妮)出嫁之日。在赶往表亲家的路上,我家三婶嘴巴甜如抹蜜,遇上行人一律笑吟吟地大声喊:“达隆哈勒俏(壮话:伯父嫁女儿),随我喝酒去啊!”被邀之人便站过路的最边沿,把路让给我们穿
那是一个远房表亲的女儿(达妮)出嫁之日。在赶往表亲家的路上,我家三婶嘴巴甜如抹蜜,遇上行人一律笑吟吟地大声喊:“达隆哈勒俏(壮话:伯父嫁女儿),随我喝酒去啊!”被邀之人便站过路的最边沿,把路让给我们穿戴花绿一团的群体,脸上也笑吟吟地:“噢,今天你们有酒喝呢。”三婶又一个劲亲热地邀:“你跟去噢,一定要去!”被邀之人便起劲地笑:“你们走先,我跟后噢!”我们也跟着起劲地笑。冬天的田间,淡黄的油菜花正迎候季节灿灿地盛开。空气里,一团喜气浓郁芬芳,用力呼吸上一口,很富足的感觉直沁心脾。
我们拐过几座土坡,又踱过高高低低的田垄,三婶才指着远处的一片竹林,说到了。远远地,看不到村舍屋角,却看见繁茂的竹林里冒出一丛二丛的炊烟,传来一声两声的狗吠鸡鸣,一条硬化水泥路延伸竹林里,指引外面的人进去里面的人出来,这才知道那是一个村落,有人有狗有猪牛马羊。
按当地的习俗,我们在村口燃放了鞭炮。一阵鞭炮炸响声过后,竹林深处跑出来一群人,他们笑逐颜开地围上来,热情地接过我们手上的东西。我手上提的是自己的挎包,里面全装私人物品。一个老妇要接过去,我连忙说:“不了不了,谢谢!”她急了,撇红了脸说:“我们礼节不周了。”站在一旁的三婶忙作解释:“她常年在外,乡下的这个礼数她不懂,达芭(壮话:伯母)不见怪噢。”说话间,三婶用力扯过我手上的挎包,很快地放到那老妇的手上。那老妇立马开心起来,拎着我的包,小跑着走在我们的最前面。那样子,就像一个完成了一项大任务的小士兵。后来才了解,迎接客人帮客人拎包是这个村庄一种很重要的待客礼数,不能有半点怠慢和疏忽。
表亲家的大门上贴着大红对联,高高挂起红灯笼。院子里的长桌圆椅上,糍粑糯饭油炸果米花糖,一盆依着一盆,,高得冒尖的顶上,抹着一点胭脂,红艳艳,喜融融。房子的走廊摆满了嫁妆,彩电冰箱消毒柜洗衣机,崭新齐整。大人手上忙碌着,脸上朝着我们笑,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互相点头打个招呼;小孩嘴里含着糖,跑进跑出,大声嚷嚷:“走咯,看达妮去!”
达妮的闺房里堆满了陪嫁的生活用品,大到床罩棉纺,小到脸盆牙膏,琳琅满目,挤得一个屋子像开杂货店。这样一屋子的生活物品,再加上走廊摆放的三大件五大件,陪嫁到婆家可真给娘家挣足脸面了。旧时,壮族女人过门,在婆家争到家庭地位的高低是由陪嫁品的数量来决定的。现今,农村的这种陋习虽然不是顽固存在了,但观念里依然残留一些或是摆场或是攀比的东西。
达妮穿着一套滚着一团喜气有凤图案的大红对襟壮家棉袄,坐在红红绿绿的嫁妆堆里,化好了淡妆的脸充满了愉悦。她的身旁站了几个年长的妇人,声音压得低低地在说话,窸窸窣窣地,侧耳细细听了才晓得,原来她们在等待为达妮梳头的女神来临。按壮家古老的传说,梳头女神是一个美丽典雅的女人,头戴花冠,裙袂飘飘,话语温柔甜美,喜欢静谧。所以在迎候梳头女神的时候,凡间俗人万万不可大声喧哗。偶有小孩不长记性的,无意间发出声响,大人便瞪大眼吓唬道:再嚷嚷,拿针线缝嘴……可我发现,达妮的头发已梳好了的,和她脸上的妆很配很和谐,想必是早先到街上美容店搞好的吧。
突然,屋外有人喊:“梳头婆来了。”屋里的那几个老妇人便紧张地迎出去,很快地就拥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,急匆匆地走进房来。那个妇人长得又白又胖,脸像只面盆,头上梳着个髻,乌油油地,左边的鬓发安插着几朵绢花,穿着一身大红的滚着牡丹图案的丝面袄子,大朵的牡丹花在她身上热闹闹地开着,显得身段更肥胖了。一线阳光从窗台上照下来,不偏不倚恰恰照亮了她的通身,看起来像铮亮的油桶,又像布店里整匹的布,跟传说里描绘的梳头女神相差甚远,我心里不免有点失望。她一进门就扭着个粗拙腰身哼哼呀呀地唱,忽儿击掌忽儿拍腿,像太极拳过招。虽然我不明白她要表达些什么,但看着她那滑稽的样子,一直忍俊不住地笑个不停。
梳头,是流传于壮族农家的一种婚嫁习俗。旧社会,为新嫁娘梳头的梳头婆都是请富人家的媳妇,仗于富门,本身也就多了三分福气。如今,农家生活好了,贫富分化悬殊不大,因此,梳头婆大都请村里或邻村装模作样的仙婆。目前,壮族农家还有大部分人对神仙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膜拜,坚持认为天上是住有神仙的,神仙从来都是吉祥物,会给他们带来安康与幸福。在他们眼里,仙婆就是神仙的代言人。
达妮端端正正地坐在镜子前,梳头婆站在她身后,右手执着把小巧玲珑的红木梳,左手做着梳理状,嘴里念念有词:一梳,烦恼掉。后面拖着“哎哎哎”的尾声,断断续续,像一只咳不出来的狗,逗得大伙肆意放声大笑起来。
“递红包!”突然有人这么一喊。早已候着的一个伶俐的小女孩得令后,赶紧递给梳头婆一只红包。
“二梳,财满缸,哎哎哎”梳头婆又唱。
“递红包!”有人又喊。
“三梳,子满堂,哎哎哎”“递红包!”一唱一喊,一惊一诧,急促无比,似欲紧紧踩住吉时良辰的尾巴,唯恐吉神还没把怀中的祝福之花撒尽就飞回天上去了。
古时,梳头婆要在短时间内把新嫁娘的头打扮成成年妇女模样,一般规定在落三次梳里完成,髻要打得结实光滑,鬓要理得平整,纹丝不乱,头饰要插得恰到好处。如果在落三梳后还做不来,旁人要鄙夷的,要么说功夫不到家,要么说贪红包贪财。现今的梳头也只是做个形式而已,新时代新潮流,壮家的姑娘理所当然接受了新娘妆、婚纱和花车等婚嫁新概念。不管怎样,乡土梳头婆的手是笨拙的,永远做不出街上美容店的那份精致。
梳头婆最后一道工序是弯腰捡拾地上的落发,卷成一团,留待达妮出门时随门外的那盆水一同往外泼。这习俗,后文说到。
可是,现当今,这道工序几乎免了。因为达妮的落发正躺在街上美容店的瓷砖地板上,被美容店老板娘的尖头高跟皮鞋绕来绕去。
冬阳西斜时分,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而来,欢声笑语,鞭炮阵阵,场面更加隆重更加热闹,喜庆气氛越发浓郁了。
守候一刻钟左右,达妮出门的吉时到了。她在喜娘的搀扶下,低垂着头,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出了闺房。
他们在堂屋里举行的仪式。堂屋的正面墙上方,摆放着祖宗神位,神台两边点着两根粗拙的红旺旺的蜡烛,毕毕剥剥地燃烧。
版权声明:本文由zhaosf123传奇新服网原创或收集发布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本文链接:https://www.yifuya.com/html/sanwen/x6d5aa5ds5iyuf4.html
相关文章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