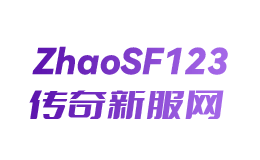
忘不了的苗市腊肉
苗市并非市,而是一个乡,它的全称是苗儿滩镇。十多个自然村疏密有致地分布在沿河的青山脚下,河中央的一条条渡船就像衣服上的一颗颗纽扣将两岸的村与村,寨与寨连接起来。从小我就喜欢到那里走亲戚,每次一下车,马
苗市并非市,而是一个乡,它的全称是苗儿滩镇。十多个自然村疏密有致地分布在沿河的青山脚下,河中央的一条条渡船就像衣服上的一颗颗纽扣将两岸的村与村,寨与寨连接起来。从小我就喜欢到那里走亲戚,每次一下车,马上跳上渡船,手里握着被摸得光溜溜的铁丝吊起屁股拉,看到船儿一步步前进,天上的云朵渐渐后退,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,把船在水面上摇晃带来的恐惧早抛到九霄云外了。真的,过渡船的感觉特别过瘾。
其实,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往大姑家跑的真正原因还不是渡船,而是苗市腊肉。
隆冬季节刚刚来临,大姑便捎来口信叫我们几姊妹去做客。每次,我们都是提前到达,亲眼目睹大姑家专喂苕藤等绿色食品的年猪被宰杀的经过。照洗车人修猪的惯例,没有破肚之前得像吹气球一样向猪身子里吹气,让它鼓得圆滚滚的,再用屠户专用的铁刮子弄干净上面的猪毛。每到此时,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孩便会拍手欢叫起来:“哎哟,好肥!好肥!”然而,姑父他们苗市人不欣赏这种做法,说吹过的猪肉里面进了空气,不好吃。他们有的是耐心,会一直把猪皮弄得白花花的才肯松手。等姑父他们几个后生把砍好的一块块猪肉扔进大木桶时,大姑将事先准备好的花椒粉、山胡椒粉、盐等佐料拿来,往热气蒸腾的猪肉上使劲地抹。她手脚麻利地忙碌着,口中还念念有词:“淹腊肉得趁热打铁,这样味才能渗得透。另外多抹些盐,俗话说‘盐多不坏滓’。”淹制完毕,然后用簸箕将木桶盖上。
过了半月之久,大姑将这些淹好的猪肉一块块挂在火坑中央的炕上熏烤。起初几天,她吩咐我们往火坑里拼命添加杂木柴,可以说是大火熊熊。等猪肉的颜色微黄,水分稍干,大家平时所说的爆烟肉便做成了。如果切上一截炒豆腐丝的话,别有一番味道。以后的日子,火炕里的火势明显减弱,用大姑的话说,不能再看见明火了。她命令我们将柚子皮、桔子皮、甘蔗渣、瓜子壳等统统丢进火坑里。这样,熏出来的腊肉额外香。冬天是农闲季节,大姑她们一般不用下地干活,所以火坑里从来不曾断过烟火。这样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开春,大概是三、四间吧,农民们到了忙着下种的时候,炕上的腊肉也变成了火柴头一般的黑。
这时的腊肉已经彻底熏干,下一步工序是传统的保管方式。大姑首先将刚从炕上卸下还不及回潮的腊肉用菜油脚子抹遍,接着把它们藏在一大堆空谷壳里。到了六月六这一天,重将它们从谷壳里掏出来翻晒,然后再让它们回到谷壳中。这样做出来的火坑腊肉即使放上几年,也不会变色,变味。
到了秋天,当屋前田坝子上打谷机声音轰隆轰隆响起的时候,大姑从仓里甩出一腿粘满谷壳的腊猪脚切开,我站在旁边看到红得似枞篙一样的瘦肉,差点流下涎水来。大姑用刀轻轻取下一截,放在火上烧好皮,然后冼净,煮熟,再切成巴掌大块大块的,炒上新鲜辣椒,再放一点大蒜,香味传遍了全寨。吃的时候,我用筷子使劲夹起一块,晃悠晃悠的,送到口里,嘴角两边流出油来……
转眼间,四十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。这么多年,我对苗市腊肉的情感,不曾有一刻钟的闲暇淡化过。
前几日,大姑托人给我捎来一些苗市腊肉,说是凭关系才弄到的,现在正宗的苗市火坑腊肉抢手得很,全被运往了外地……
我暗自庆幸:沾大姑的光,又可以大饱一番口福了。
版权声明:本文由zhaosf123传奇新服网原创或收集发布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本文链接:https://www.yifuya.com/html/sanwen/x7i9969759su2tu.html
相关文章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