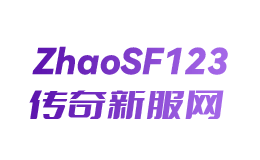
断送一生憔悴,只消几个黄昏
这是一个流传深远的爱情故事,也是一个始乱终弃的原始悲剧。可是,每次翻开那泛黄的书页,我总能想到许多同类故事所不能想象的东西;每次合上书卷,又是那么惆怅、哀怨,久久难以释怀。
崔莺莺,虽然她的真实姓名、身份早已被历史的风尘所湮没,但她那曲凄恻哀怨的恋诗足以让她流芳百世。
莺莺美貌,“常服睟容,不加新饰。垂鬟接黛,双脸销红而已,颜色艳异,光辉动人”,连“未尝近女色”的张生(元稹)也一见钟情。莺莺有才,身为才子的元稹居然赞美她“大略崔之出人者,艺必穷极,而貌若不知;言则敏辩,而寡于酬对。待张之意甚厚,然未尝以词继之。时愁艳幽邃,恒若不识;喜愠之容,亦罕形见”。古人评女子以德容工貌,评男子以恭俭温良让,限于篇幅,工、俭不知如何,但其余七项美德,元稹一气都许了莺莺,以元稹的才气能如此赞许莺莺,料不是虚得。况且,后文莺莺之琴声,莺莺之书信,声声如泪泣下,字字如血滴下,亦知此言不谬。我想,元稹自言“性温茂,美风容,内秉坚孤,非礼不可入”,一生倚遍温柔瓣,惟独对莺莺刻骨铭心、终身难忘,大概不是自己有负她而内心有愧,而是莺莺的才华至斯,是唯一真正的知己。
历代的弃妇总是可悲,同时又是可鄙的。被抛后,或仍心有不甘、纠缠不情,如陈阿娇;或只有恶毒的怨恨,如霍小玉,“我死之后,必为厉鬼,使君妻妾,终日不安”……而莺莺最动人之处,便在于能为自己所爱的人着想,而不从自己能否占有他出发。离别在即,一次是“崔氏宛无难词,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。”,另一次是她安慰他:“始乱之,终弃之,固其宜矣,愚不敢恨。必也君乱之,君终之,君之惠也;则殁身之誓,其有终矣,又何必深感于此行?”可见莺莺对于自己的结局是有预感的,所以我曾天真地揣测,“崔氏甚工刀札,善属文,求索再三,终不可见。往往张生自以文挑,亦不甚睹览”不是元稹“忍情”,而是莺莺“忍情”,她是在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成全所爱的人。后来,即使明知是始乱终弃的结局,依然劝他“慎言自保,无以鄙为深念”;即使面对命运的不公,她也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劝他“还将旧时意,怜取眼前人”……这是她的高尚之处,也是她的悲哀之处。
元稹,很多人骂他负心薄幸、道德卑劣。他不但负心薄幸、始乱终弃,甚至还说出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,不妖其身,必妖于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贵,乘宠娇,不为云,不为雨,为蛟为螭,吾不知其所变化矣。昔殷之辛,周之幽,据百万之国,其势甚厚。然而一女子败之,溃其众,屠其身,至今为天下僇笑。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,是用忍情”这种令人所不齿的言语。
但他亦不过是一个悲剧,一个更深沉的悲剧。作为一个女子,我痛恨那些花心、薄情的男子,如李益、薜平贵等。但是看了有关元稹的故事,我却始终无法恼怒,虽然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入仕之前,他常以松、竹、玉咏怀,应当是一个才华横溢、清高自傲的文人。我想,这也是莺莺对他一见倾心的原因吧。在《莺莺传》中,有一段故事耐人寻味。莺莺邀他半夜悄悄约会,他却把睡着的红娘叫醒,于是风花雪月变成了冷冰冰的说教。显然,他此去的目的不是苟合,而是当面吐露衷肠,依然是谦谦君子。当他初入仕途、身为下吏时,他“数上书言厉害,当路恶之”,依然是一个疾恶如仇、正直耿介的清官。可是,统治者的昏庸、权贵的谗言、长期的贬谪、世态的炎凉,让他渐渐学会了委曲求全、左右逢迎。于是,他开始依附宦官、结党营私,由此平步青云、呼风唤雨。他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,虽然这个过程并非如他所愿。就在这时,他纵情声色,写下了大量的艳诗。在这些华美的诗篇中,没有了早年的心存高远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落寞和深深的绝望。
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永远无法得知,只有在“寄情”“言志”的诗篇中,或许能窥测一二。一向自诩风流的他,对于韦丛,他是“唯将终夜长开眼,报答平生未展眉”,更多的是愧疚;对于薛涛,他说“锦江滑腻峨眉秀,幻出文君与薛涛”,更多的是敬仰;而对于莺莺,则是一生的怀恋。于是,他大张旗鼓的写下了凄怨悱恻的《莺莺传》,并且对于莺莺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负心薄幸基本上遵循了事实,除了最后的强词夺理稍有掩饰以外。历代的负心汉,比元稹更下作、更苟且、更卑鄙、更无耻大有甚者,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、笔之以墨,供认不讳的傻瓜是很难找到的。也许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始乱终弃,对于莺莺也并没有愧疚和自责,毕竟这样成就了他的功名利禄。然而,“情之所系,爱之所在”,经过时间的延伸,经过空间的移位,最令他魂牵梦萦、激荡心扉的仍是那位“殷红浅碧旧衣裳”、“满头花草倚新帘”、“为见墙头拂面花”、“二十年前晓寺情”的莺莺。也许,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,这个被他抛弃、想忘却不能忘的女子,仍然隐隐绰绰地浮现着。这样的结局,对他来说,何尝不是一种惩罚?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我想,写出这首诗的元稹,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,比之当下某些蝇营狗苟的时人,尚有过人之处。
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中“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”的愿望是美好的,但不切实际。如果要我选择,我更喜欢《莺莺传》,尽管有些残酷。
版权声明:本文由zhaosf123传奇新服网原创或收集发布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本文链接:https://www.yifuya.com/html/sanwen/x9o5iaado58uf11.html
相关文章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