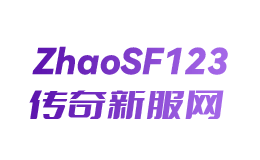
清平镇
前言
本故事纯属虚构,乃是收集同学回忆,加上一些对现实社会现象的感悟而作。虽是小说家言,但也有许多真实之处,不过故事有的地方却有夸张之嫌。故事记叙一个在外拼搏的年轻人,觉得生活欺骗了他,当然罪魁祸首是社会。于是在心灰之时,想回到那个儿时带给他无数快乐的家乡。他的家乡像人世间的最后一片伊甸园一样静静地躺在乌江边上,可是好景不长。瞬间就被残酷的摧毁了。也表现了主人公,对在城市寻不到根而家乡已不复存在的不解,以及对命运的无可奈何,和对社会的批判。
一
我的故乡是个很穷的地方,实实在在最穷的地方。原本中国就已经很穷了,偏偏我们省是中国最穷的省,我们地区又偏是省里最穷的地区。可最不幸的,我们镇又是我们地区最穷的一个镇。总而言之,我们那就是这个世界最贫穷,最底层的地方。
关于故乡,我的心情很复杂。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的,或者该把自己摆在哪里。在中国不带身份证,你都不能证明你就是你自己。所以我只能把我呆得最久的地方,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称作我的故乡。
在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化,甚至更胜于美国的种族歧视,就是地域歧视。发达地区嘲笑发展中地区,发展中地区嘲笑落后地区,落后地区的都相互嘲笑。我想这应该值得社会学家关注,可以好好研究一下,没准会得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成果。
我原本是个重庆人,后来搬到贵州,就听到其他小孩臭屁地指着我骂道:“四川佬(重庆以前属于四川)吃稻草。”这话听起来并没怎么显出不友善,可当你知道稻草在乡下是用来喂牲畜的,那你就可想而知其中的含义之丰富了。
到了大学,人家却歧视贵州。总是问你们贵州通电了吗,有火车吗,你们怎么来上学的?我通常回答道:“我们都是骑着牛来上学的。”但问的多了,我有时不得不把原籍搬出来当挡箭牌。因为在他们心中重庆又要高出一个档次。我工作后,到了那些所谓的发达城市。他妈的我又成了乡巴佬,土包子。
都是太阳底下的禾苗,哪有什么高人一等。大家还要头挨着头,肩并着肩一起活呢。没有谁比谁更高贵。
上海和北京是中国内地最大、最发达的城市了,所以在他们眼里,其他地方的人自然而然就都是土农民了。这是一种骄傲,至少外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。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想往那里头扎,哪怕挤成了一缸豆酱。也要在这个穷国家里最不穷的地方买一套厕所大的房子,也就死得其所了。
这样,奚落那些穷地方的人也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。也只有这样才会让自己有一种优越感,才能活的很幸福。尽管那确实不是幸福的,但至少大多数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。这就有关中国另一个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——面子问题了。
面子问题和官场,是中国的两大特色。面子不光每个人要,而且整个国家也要。所以国家会不惜一切地拔高自己,于是新建了很多东西,举办了很多大会。这是要让世界,至少是中国人,认为我们很强大,我们很富裕,我们很幸福。
但我,是真的不幸福了。所以我跑回了我的家乡。它静静地躺卧在乌江边上,和那昼夜不舍的江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名字——清平镇,这里确实清平安乐。原因是这里发展落后,经济不发达,有的人由生到死都没离开过这里一步。那些见过大世面的人,觉得这里太穷了,所以又叫它“清贫镇”。
镇里只有有唯一一班汽车跑县城,车子早已锈迹斑斑,可开起来马力依然很足。像头永远不想退休的老牛。
回镇的一路上,风景没什么大变化,依然小时候的摸样。只是这个时期看不到丰收的忙碌,只是兜满了一车稻香。人们话不多,各自望着窗外,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车唯一的变化,就是司机不再是原来那个有一脸络腮胡的豪爽老头了。他看起来样子凶神恶煞,但心地是极好的。
有时候在半路遇到拦车的老人,即使一毛钱没有他也会搭载一段。他声音很大,有时候就像拿了个喇叭在吼。而且喜欢和外出的年轻人聊一些新鲜事,当然他也爱谈起他在外漂泊的经历。但他很喜欢自己的家乡,把所有赚来的钱买了辆车,就是不愿再外出。他的故事很多,他自己讲得也很动听。但大多数我都忘了,依然记得的是他的背影,这背影仿佛有许多故事要说。
不过现在,坐在那的是个年轻人。依稀记得是老司机的儿子,只是在我记忆里他还是那个流着鼻涕的押车小子。我走过去,递给他一支烟,问道:“你老汉呢?”他侧过脸看了我一眼,淡淡地说:“死了。”没有悲伤,也没有喜悦。这就是淳朴的乡下人,没有花言巧语,只有朴素且粗超的感情。
我没敢再问下去,他究竟怎么死的,什么时候,都不重要了。我返回去坐在窗户边,看着从眼前一晃而过地树木。没什么比死更令人沉重了,也没什么比死更令人信服他的离开了。
我突然想到,我们就像窗外的那些花草树木。还没来得及向世界展示自己,就一闪而过了。
直到枯死我们都没有被这个世界欣赏。
二
镇上的布局没什么变化,依然是东西两条大街,简单的出奇。加上北边的山羊坳,以及南边的商业街就是整个清平镇的全貌了。其实所谓的商业街不过是逢2,4,6的赶场街罢了。除去走到这的那段路程,可称得上是简单的“物物交换”,农民把家里的家禽牲畜,粮食菜蔬卖掉,再买上一些必用品带回家。
最多会在镇上多呆一会儿,等几个熟人。“四四六六”一番,也不喝多,了不起一人二两。在我们这请人喝酒是个体面的待客之道。无论是在人家里,或是在大街上相遇,都可以此道待之。除了酒,烟也是必不可少的,老人抽旱烟,共用一根烟杆则显出对人的充分尊重。你若不抽,便就有不敬之嫌了。
当然,年轻人们都爱抽纸烟。关于这些场景我是最熟悉不过了,因为我家就是卖杂货的。每逢赶场,人们除了来我家买些杂货。大多数就是在我家门口聊聊天,叙叙旧,我家门口坝子上老早就
版权声明:本文由zhaosf123传奇新服网原创或收集发布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本文链接:https://www.yifuya.com/html/xiaoshuo/x58da7ada8s3t3g.html
上一篇:锦书轩征文:《失踪的宝石》
下一篇:我的暗恋,你还记得吗?
相关文章
